上映前夕, 特地從台北南下高雄, 親自去找阿共的姊姊, 邀請她來看阿共(她弟弟)的電影。
我把紙本簡介交到她手裡, 封面是一張阿共獨自行走在高山芒草推上的照片。 搖曳的草海, 孤獨的背影, 姊姊才剛看見, 淚水汨汨而下, 心疼弟弟走過的顛簸與坎坷。
她一邊掉淚,一邊又忍不住挖苦弟弟的人生荒唐。或許這就是愛吧,愛也帶著責備,也落在最深的牽掛裡。
或許,《高山遊民》也是一部這樣的電影,在山的孤獨裡,看見人如何走過荒謬與跌宕;而在家人的眼淚裡,感受到愛的矛盾與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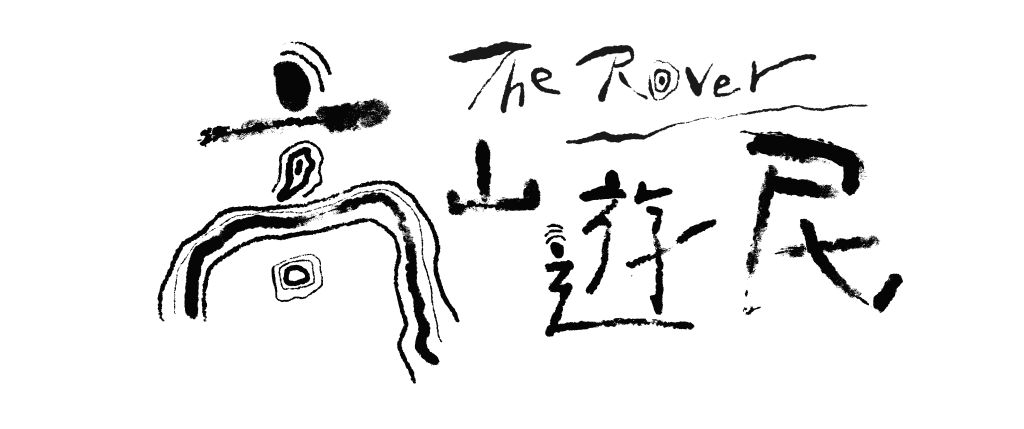
上映前夕, 特地從台北南下高雄, 親自去找阿共的姊姊, 邀請她來看阿共(她弟弟)的電影。
我把紙本簡介交到她手裡, 封面是一張阿共獨自行走在高山芒草推上的照片。 搖曳的草海, 孤獨的背影, 姊姊才剛看見, 淚水汨汨而下, 心疼弟弟走過的顛簸與坎坷。
她一邊掉淚,一邊又忍不住挖苦弟弟的人生荒唐。或許這就是愛吧,愛也帶著責備,也落在最深的牽掛裡。
或許,《高山遊民》也是一部這樣的電影,在山的孤獨裡,看見人如何走過荒謬與跌宕;而在家人的眼淚裡,感受到愛的矛盾與重量。
「你們好,歡迎來到三六九,現在有薑湯跟綠豆湯!」
帶著濃濃台灣國語、 滿身朝氣的聲音, 迎接著我們這群氣喘吁吁的登山客。
他叫「阿共」, 是一名高山協作員。
在山屋裡, 只見他俐落地拿起鐵盆, 食材一道道下鍋, 不一會兒就炒出一盤熱氣騰騰的菜香。
在三千多公尺的高山上, 能吃到熱食是種無與倫比的幸福, 不只是味覺的滿足, 更是對一段艱難路程的慰藉, 與再出發的力量。
晚霞清晰如畫, 點點繁星也悄悄亮起。
山友們陸續走進廚房, 好奇今晚的菜色。
「盡量ㄘ、盡量ㄘ,今天煮了三肉四菜一湯!」
阿共的熱情, 似乎連低溫都融化了, 山友們圍坐一圈, 開懷取菜。
「靠夭,今天大家是夭死鬼?竟然吃完了!」
笑罵聲裡, 他又端起鐵盆, 迅速炒出一大盤炒飯。
屋裡熱氣蒸騰, 談笑聲不絕, 窗外雪光閃爍, 亞熱帶的我們在異常興奮中, 像極了放學前的孩子。
夜色漸沉。
阿共站在不遠的坡上, 一邊抽著菸, 一邊望著即將隱沒的晚霞。
遠遠的, 只見紅光一閃一閃。
「阿共,你抽長壽喔?」我湊上前。
「這樣你也聞得出來?」
「而且還是黃長壽吧。」
不是我聞出來的,是那菸盒從他口袋裡露出一角。
「怎麼不跟大家一起吃飯?」
「我邊煮邊吃啊,早就飽了。」
「一次上山都要待多久?」
「有時一兩個禮拜,有時一個月。」
我這才明白 協作員的工作不只是勞力, 更多的是孤獨的考驗。
「遠看是銀行,近看是牢房啊。」
阿共丟了一支菸給我, 自己又點上一根。
「歹勢啦,我只抽長壽,以前在監獄就抽習慣了。」
這句話的語氣忽然變得平靜。
原來他曾經入獄, 判刑時未立刻服刑, 逃進玉山避難, 警方也懶得上山抓人。
兩個月後, 他自己下山自首。
「還是山上比較自由啦,至少有你們這些來來去去的山友,陪我練瘋話~」
他大大吸了一口菸, 又慢慢吐出。
人生, 是為了生活而忍, 還是為了自由而忍?
看似灑脫的阿共, 身上藏著兩種相反的命運:被山收留,也被山困住。
但想想, 多數身在平地的我們, 不也一樣在這矛盾之中?
上山最終的目的, 永遠是安全下山。
這次拍攝, 是我第一次在如此嚴峻的環境裡工作, 偏偏又遇上寒流。
不只是身體的挑戰, 還有器材的耐寒、 耐潮、 電池的續航, 一切都在極限中進行。
感謝兩位夥伴李志煌、 陳俊逸, 一路幫我分擔重量、 提供想法, 也守護著安全;
感謝留守人孫穩翔, 在山下時刻關心我們的動態。
這趟能順利上山、 平安下山, 靠的不只是努力, 還有許多人的托付與守護。
謝謝每一位朋友, 也謝謝山神。
要前進大霸尖山之前, 必須先走過 17K 的林道。
這段路沒有陡坡, 卻漫長得幾乎沒有盡頭。
一早從登山口出發, 天色還微微灰, 林道入口被薄霧籠罩, 腳下的碎石被夜露打濕, 踩下去會發出悶悶的「喀」聲。
山風帶著泥土與松針的味道, 偶爾傳來不知名鳥鳴。
背上的相機包壓得肩膀生疼, 每一步都像在秤重量。
「這裡明明是平路,卻比爬坡還累。」
沿途經過崩塌處、 倒木、 幾段被溪水沖斷的碎橋。
每一次繞路都得小心踩著岩石邊緣前進。
太陽升高後, 霧氣散開, 陽光落在山壁上, 映出一層灰藍的光。
偶爾會遇見返程的山友, 臉上都帶著被山風吹洗過的神情。
中午時分, 我們在一處溪邊休息, 打開行動糧, 簡單泡了杯熱湯。
氣溫不到十度, 湯香混著山氣, 成了難得的奢侈。
抵達林道終點時, 手機訊號忽然湧入, 震動聲此起彼落。
鋪天蓋地的新聞標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我念出手機上的文字:「誒……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了,坦克已經開進基輔。」
我們面面相覷。
走了五個多小時、 以為遠離塵世的山林, 忽然被現實穿透。
身在台灣, 戰爭好像很遠, 又好近。
一場在世界另一端的侵略, 卻讓我們想起那些討論台海的新聞。
那一刻, 我們都默默停下腳步, 聽著風。
「哪天會不會換我們打起來了?」
沒有人說得準。
「如果真的打起來,有什麼打算?」
「衝前線啊!」
「在深山?」
「拍個紀錄片。如果怎麼樣了,就留給後世人剪吧。」
我想, 這樣的對話, 大概就是我們這個世代的縮影。
假想敵太真實, 和平太脆弱。
「下山之後,世界會不會變得不一樣?」
一樣, 沒人說得準。
簡單用完午餐, 收拾好裝備, 也收拾好情緒。
帶著滿身乳酸, 繼續往上攻那段 4K 的陡坡。
空氣愈來愈薄, 呼吸聲愈來愈重, 背後的林道越來越遠。
雲海在腳下翻湧, 像另一個世界。
———
幾天後回到台北, 夜裡遠望 101 大樓,
那面亮起的烏克蘭國旗, 在霧氣中閃爍。
我想, 如果有一天台灣也是不得不面對戰爭
凌晨五點多, 一通電話打來。
剛從深山回來的我, 疲憊還沒退, 腦袋昏沉, 被突如其來的鈴聲吵醒, 心裡暗罵:「是哪個神經病?」
螢幕顯示, 阿共仔。
啊, 原來是那位我拍紀錄片的高山協作。
這時間他打來也合理。
阿共半夜得起來為山友準備早餐, 也許忙完一輪, 閒閒沒事想找人聊天。
我心裡雖然幹聲不斷, 還是接了。
「安仔,起床了沒?」
「靠夭,當然還沒。」
「你紅了啦!現在大家上山都要找我拍照。我本來就夠紅,被你弄一下更紅!」
他那口氣, 八成是誇飾。
前陣子上傳的《高山遊民》在山林圈傳開, 點閱比我預期的還多。
影片被看見是好事, 但此刻我只想睡。
阿共開始天南地北亂聊, 我在夢囈之間咦咦啊啊地應著, 聊了五分鐘, 像是又回到山上的夜裡。
掛上電話, 腦袋清醒了, 身體還是沈甸甸的。
忘了剛剛聊了些什麼, 只記得那份熟悉的自在。
想起第一次拍他時, 還真難靠近。
看似熱情, 其實身上有一道厚牆。
或許他覺得我太嫩, 不想多講; 或許他只是習慣保留。
但後來幾次上山, 他漸漸明白我拍的, 不只是「高山協作員」的職業, 而是他這個人。
他開始鬆開偽裝, 讓我看見熱情底下那些傷痕。
紀錄片這行, 真的很吃「人」。
有時我也會迷戀那種「一點一滴被打開」的過程。
經營關係不易, 消費與真心之間, 往往只差那麼一線。
而別人願意給我信任, 我就有責任說出一個真實的故事。
只是, 阿共啊
下次打電話, 別挑凌晨五點。
想當個稱職的遊民, 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早晨的山莊靜得出奇,
阿共在院子裡餵雞、 餵鴨, 也餵那群亂竄的鵝子。
飼料落地的聲音, 比山風還清楚。
他一邊碎念、 一邊笑, 像在對牠們說話,
我們在旁邊拍, 鏡頭拉遠,
只剩他、 幾隻雞鴨鵝, 和一片白霧。
那一刻, 看起來什麼都沒有發生,
卻好像, 這世界也只剩下他。
說是辛苦嗎?
其實也滿樂在其中。
拍攝的路途總是漫長,
偶爾遇到好奇的山友問我:「你在拍什麼?」
有的說早在網路上看過短片, 期待長片快點上映;
還有的在狹路相逢, 一眼就認出我和阿共。
那一刻忽然覺得,
這幾年在山裡的耕耘, 好像真的開出了一點花。
只是, 路途依然艱辛
對我、 對阿共、 對每個願意陪我一起上山的人都是。
「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個山丘。」
——李宗盛
山裡的光, 也可以是一門建築學。
某些雲的形狀, 像被光雕出的尖塔與列柱;
當太陽從下方升起, 或自嶙峋的岩脊背後射出,
就會形成一道扇形的穹頂。
每次望向群山, 都是一次巨大而精密的感官體驗。
人物的行徑各自不同, 但那份心意, 卻同樣深邃。
近來因拍攝而頻繁上山, 更能體會「上山拍片」的不易。
除了環境的嚴苛, 體力能否跟上、 技術是否到位, 都是影響成果的關鍵。
這與平地拍攝完全不同 我們沒有像《群山之島 不去會死》那樣的劇組規模,
只能靠一次次鍛鍊與累積。 下山後立刻檢視素材,
再決定下一次上山要補什麼、 改什麼。
標準很簡單:用時間換取金錢。
今天和攝影師一起看了一整天的素材, 討論哪些段落還需補足、 哪些拍法可以再精進。
那過程像是重新走過一遍山路 一邊檢視畫面,也一邊檢視自己。
除了耐心 更需要一點愛。
每次重看素材, 都會生出新的感受;
有了新的感受, 就會有新的懷疑;
在懷疑裡, 又找到新的方向。
「就是不知道拍什麼才好看啊!」
我想, 從事紀錄片的人應該都懂這句話的滋味。
有一萬種剪法, 也有一萬種重新理解世界的方式。
若拍前與拍後的想法始終如一,
那作品, 也就不會再向內生長。
保持未知的興奮感 那是山教會我的事。
大概下午三點, 氣溫開始從二十度驟降到個位數, 甚至逼近零下。
在九九山莊的幾天裡, 這樣的天氣變化幾乎是日常。
說到登山, 我們早不是新手, 但也稱不上高手。
會爬的怪物太多, 而能長時間待在高山上的人, 恐怕不多。
也因為開始在山上拍攝, 我才有機會這樣久留
能與莊主共飲烈酒, 也能用不同角度觀察來來去去的山友。
當時間被拉長, 身體開始適應, 心也慢慢融進環境裡。
不再只是過夜的旅人, 也不再只是為了撿百岳而來。
我得與不同的人打交道, 建立關係, 學會傾聽山的節奏。
久了, 竟覺得自己也開始流著同樣的氣息。
明明沒爬過多少山, 卻不知何時多了股「老山猴」的氣場。
Moving on.
這趟玉山行,
因陳文祥大哥的牽線,
認識了劉居賜大哥,
大家都叫他 Kizu。
他不僅是我們紀錄片主角阿共的老朋友,
更是名副其實的「老山猴」。
Kizu 大哥年輕時便投入高山協作,
後來進入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至今三十三年。
等於一生都獻給了山。
他熟知阿共的起起落落,
也見證過那個年代的登山樣貌。
「你不要看阿共髒髒的,像個流浪漢,
我在玉山這邊遇到山難,他都是衝第一!」
Kizu 大哥說話的眼神極為熾熱,
彷彿又回到那些生死交錯的時刻。
「軟的屍體要這樣扛、已經僵掉的屍體要這樣背……」
他邊說邊比劃,
動作俐落,
讓人幾乎能感受到那股寒意與重量。
我的登山經驗其實不長,
但因為拍攝紀錄片的關係,
這一年多來與夥伴頻繁進出深山,
也因此接觸到許多台灣山岳界的前輩。
他們不只是登山運動的開拓者,
更是台灣山林文化的守護者。
在高山這樣極端的環境裡,
他們的知識與判斷,
是許多人能平安下山的理由。
當山中發生意外,
往往就是這群「人肉救護車」第一個衝上前線。
他們是山裡最強韌、
也最寂寞的存在。
從 00:00 秒開始組織長片,其實是我最抗拒的階段。
第一次海量時間剪接、
第一次要消化海量的素材、
第一次組織長片……
好多好多第一次,
好多好多不知從何開始的開始……
彷彿是《世紀帝國》的黑暗時代,
得靠著斥侯一步一步拓荒。
從無到有,是如此難消受卻又樂在其中。
就像影片其中一段情節:
卓:「文祥來定方位,阿共你來帶後面的消防隊,我來開路!」
這段是角色在回憶高山搜救的過程,
完成一件大事需要分工合作,
一個人無法成為英雄。
亦如剪接,組織的過程需要大量的丟接球,
需要夥伴彼此通力合作。
也因此,當與一個看法、觀念相近的夥伴交換感受與想法,
內容最後增加的豐富程度,
往往會超越當初所設想的。
這時都覺得感恩能遇上這夥人。
而另一個好處是,
在洞察新觀點,或是需要打破某些成見時,
這樣的合作是精神上的支持,
也是安心的訊號。
影片終於有些雛形了,
心也比較安定。
雖明白影片後續會不停打磨,
但至少經歷過了那種摸不著邊際的徬徨。
時間是紀錄片之神。
拍攝幾年下來,
老協作快揹不動了,
於是換我扛兩百斤麥子,
十里山路不換肩了(?
我想我也成為卡里布灣團隊。
阿清老闆,
這樣可以贊助《高山遊民》劇組嗎?
他們的車至少塞了快三百公斤的工具及食材,
要從埔里出發前,
小婷跟吾明兩位高山神雕俠侶想去吃點好料。
吾明:「我們上山前,都會先吃一頓我們想吃的,因為上山就吃不到囉。」
乍聽之下,有夠像要入監服刑(?
但這一句話,確實深深觸動了我。
我知道每一趟上山就是得要跟便利的平地隔離一陣子;
這跟一般登山客的心境完全不同。
通常登完山之後都會大吃一頓, 當作慶功, 先苦後甘。
而他們卻得先甘後苦。
這樣的工作型態也很像船員。
每次哥哥上船,我也很想念他。
然,我們就兩台車一路從埔里切向中橫,
繞過合歡群峰, 再繞過梨山、環山。
這之間海拔起起伏伏、 有雲有霧、
且短時間的海拔攀升, 都能明顯感受到濕度的變化。
車程走了五小時,
我們就睡在雪山登山口,
喝了點啤酒, 仰望星星,
敬祝今天勞累, 等待黎明再起,
還有一段山路要走。
拍高山協作默默地邁入第三年了。
當然這過程認識了很多高山前輩朋友、
也當然有了些小特權,
但我想, 最可貴的就是身上也漸漸染著他們在高山的氣。
我跟夥伴俊逸說:
「真的從未想過,我們開始決定拍高山題材,竟然會走到這一步。」
從產業面走到社會面,
再更深入的進入家庭面,
拍攝的觀點越來越全面。
相對,要處理的面相也就越來越複雜,
越得小心翼翼,怕一不小心作品就流俗了!
這次大地震幸好沒讓雪山有太多災害,
高山協作依然可以安全縱遊山間。
這趟下山,小婷問起:
「你們真的要下山囉,什麼時候再上來?」
突然被小婷的發問拉回現實。
是啊, 差點以為混久了就是同一群人了;
但實質上, 還是各有各的任務,
終究得別離一陣, 日後再見面。
我想, 這也是拍紀錄片得面對的抽離感吧。
山永遠都在,
而山讓我們相遇, 必有祂的道理。
今年七月去綠島,
認識一位潛水教練,
得知我常駐高山拍攝,
他也想體驗看看空氣稀薄的感覺。
這次上山,
潛水教練跟協作大談「山」「海」經,
彷彿當初像我初登山的模樣。
「你們(協作)扛物資上山,就像我們揹氣瓶下海一樣吧。」
「海底的海葵、海龜應該就像我們看到黑熊、山羌吧!」
把潛水教練從水下三十公尺,
拉到海拔三千公尺還滿有成就感,
也謝謝幫我揹了五公斤的腳架,
少流了三公升的汗水⋯。
在頒最佳紀錄片時,
謝盈萱說了一段話。
這段話雖已深知它的道理,
但在金馬典禮聽到,
有一種深深被接住的安慰。
或許大家都是說故事的人,
惺惺相惜吧。
「我們當演員,可以躲在角色背後,但拍紀錄片完全要跟被攝者一起經歷。」
是啊!
中央山脈海拔三千多公尺的各山頭上,
氣溫五度下,
有時雨勢及風勢也不小。
這其實都是意料中的事。
我告訴俊逸:「我們好像很少在山上天氣不好的時候拍攝,難得有憂鬱的景色也不錯。」
只是折騰了點……
有幾天, 我們身在三千多公尺的迷霧中拍攝;
也有幾天, 山神給了我們明亮有詩意的大景。
十秒鐘, 會發現眼中有些黃土、 有些箭竹、 還有帶灰的雲霧。
十分鐘, 會發現灰霧漸散, 陽光一塊一塊灑落, 變得明亮了, 箭竹也鮮活起來。
三小時, 除了各種不同顏色外,
發現靜止不動的山,
短短幾個小時有各種的風吹草動。
我跟俊逸說:「我們好像也很少有機會可以在一個山頭定點好好拍攝。往往因為趕行程,很少在一個地點駐足太久。」
眼前景致已足以令人心醉, 樂在其中,
而眼前宏偉的山景……
此刻, 誰能不讚嘆抬起這些山巒的神奇力量。